肩並肩坐在開往大甲的公車上,你絮絮叨叨,數著短短幾年來的每一次失望。
烈日肆無忌憚燒灼我們裸露的手臂,試圖將褲管裡的大腿熨熟,熱浪屏開頭頂轟轟作響的冷氣,貪婪地舔食人們的體溫,將熱流灌入怒張的毛孔。左前方,一位將自己曬成乾枯黑松木的婦人,有棄日夸父的凜然,徒留一身火熱的餘痕,縮在陰影之中沉默。
一車世界,半陰,半陽。
不到盛夏,已熾熱得令人腦門發暈的陽光,落在你身側。
你拿起傘,只稍稍撐開了傘面,遮去辣貼上面的燦金流火。於是,一朵皺縮的桃紅壓抑盛開。
沉默竄動在忽冷忽熱的氣流,而我們胸中伏著業火,隱隱燃動。
你的失望,是自翡翠觀音像上剝落的螢綠碎塊。
我說啊,傷心迷茫的時候,就想要拜拜。但一開始,我們誰也不曉得該往哪走,癡癡在站牌下等著可能不再存在的班次,目尋過路公車額上每一面路牌上的數字,卻始終沒見著令人欣喜的排列組合。
躲在站牌庇蔭中的我們,其實都不明白,究竟撲襲而來的熱氣之中,隱藏了什麼隱形的妖魔,只是眉梢懸憂、唇角掛鬱,結了一臉愁雲。
你說啊,你沒有聽神的話。但一開始,我們誰也不會明白一湖晶瑩的反面,不會明白其下水流如何暗湧,而黑長水草間,又藏了多少頸脖緊扼的生命殘形。
我的失望,是自牧歌詩裡垂敗的字句。
那座被煙燻得焦黑的大廟一直都在,從未來過的我們,卻如久居外地終於返家的遊子,自在穿梭於人與人,人與廟柱,人與神靈之間。
越往內殿越濃的煙霧,嗆得我濕了眼眶,來不及仔細凝視供桌後那張細眼寬面是黑是白。身前手握四柱香的你正喃喃,並非自語,而正對話。許多人和你一樣,正喃喃對話,額上汗水珠簾般垂掛,艷陽的殘印並未在此蒸發,更執著、無形的熱散放、團聚,成了散逸不去的思考、委屈、悲傷、迷茫,和高揚得將理智扯在手裡把玩的喜悅。
總走在前頭的腦子,這回退居幕後。我被心牽著走,第一次跪在了台前,擲出一個漂亮的聖盃。
你仍縮著肩,站在一團團伏身跪拜的人身側,喃喃著晃動腦袋,像已訴了三世輪迴。就像他們,就像我。
一張輪迴的網鋪展,巨大而深遠,你我不過是網角垂掛著的一陣微弱顫抖。但我們都熱愛掙扎,更熱愛找尋意義。你說,是嗎?
走吧。我說。
回家去。
你一頭臉破碎。
我一腰背喪氣。
一紙籤無法解釋所有種種,能給的只有安慰。
從來非親非疏我與你的連結,深淺不一,色調相同。
不過幾年,我們卻都明白了,人與人之間有一種親密的交談,叫恨。
寫者:黃淑真 (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
文筆不拘,請隨意發揮。
來信e-mail: lmcsilver@gmail.com
新聞來源:世新-台灣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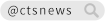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