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逸璇、謝德瑾 / 台北市
「莎士比亞的作品是經典名作,但關我什麼事?」時常是觀眾對於舞台劇的疑惑。於是,四把椅子劇團把與當代台灣切身相關的元素,例如近年中台關係以及華人孝悌觀念,一一放進作品裡頭,甚至重寫契訶夫、易卜生原著的西方經典劇作,將本地脈絡偷渡進從古到今的人性劇本裡頭,演出不只精彩絕倫,更是發人深省的故事。
期待成為劇場交椅的中二少年

「四把椅子」劇團,在十多年前由許哲彬和一群同為台藝大戲劇系的學生組成。最初的四把椅子,只是四個喜愛劇場的好朋友之間的玩笑話:「你以後當劇場界的第一把交椅,然後你、你和你是第二把、第三把交椅、第四把交椅。」在學時期,四把椅子就已存在並一起創作,而當畢業之後,對劇場仍有興趣的眾人,決定申請政府立案,成為正式的劇團。
「在十年前、我那個年代,台灣大部分選擇戲劇系的學生,其實都不太了解戲劇系是什麼。」許哲彬說:「大家帶著一個『可能跟電影電視、成為藝人有關』的模糊概念進去。」而大家入學後才恍然大悟,戲劇系的領域,原來是劇場。生長在中南部的許哲彬,自己正是這類型的戲劇系學生,原先想讀廣電,卻誤打誤撞在進入劇場後,才意識到廣電和戲劇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
許哲彬表示,自己看的第一齣戲,也是在來了台北之後才接觸到的。在台灣著重升學體制的氛圍裡,藝術教育幾乎是被犧牲掉的,也因此學生及民眾普遍缺乏藝文素養。即便課堂有安排藝術課程,也都只是用生硬不靈活的教科書填鴉,因此許哲彬認為,真正培育自己藝術涵養的,是大學時在公館咖啡廳打工的日子。
該咖啡店是過去九O年代,台北非常重要的藝文場所,而當時在此打滾的文青,如今在各個藝文領域是深具影響力的人物。「也因此我在那個咖啡店打工的時候,從他們和老闆身上汲取到很多書籍、音樂、戲劇等等的知識,其實那個時期,我才真正大幅度地在藝術層面有所長進。」許哲彬回憶。
不能用觀賞電影的方式看待劇場

由於台灣的文化及社會氛圍中,藝文往往不會被當作是日常的一部分,也因為沒有深厚的藝術認知,台灣人也較習慣電影敘事,劇場內的表現手法相對抽象,對大眾而言既抽象又模糊,以致於劇場與生活帶有隔閡,關注表演藝術的客群成為小眾。
「我們會想跟觀眾對話彼此有興趣的事情,所以我們近年都傾向採取跟當代社會較為切身相關的題材。」許哲標表示,劇團將比較接近台灣人生活的內容加入戲劇中,比如說,二O一五年的《全國最多賓士車的小鎮住著三姐妹 (和她們的 Brother) 》,故事背景就設定在中南部土豪家庭的家道中落,裡頭還隱約提到近年與中國在政治上的尷尬關係。
「這件事情對所有台灣人來說,都是可以即刻辨認出的事情,畢竟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這是四把椅子劇團成員們的共識。
當經典名著發生在當代社會

《全國最多賓士車的小鎮住著三姐妹 (和她們的 Brother) 》改編自俄國劇作家契訶夫的《三姐妹》,原著背景為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俄國,一群活在小鎮莊園裡的人,渴望去莫斯科想去城市裡面工作。
重寫的版本則將《三姊妹》的時空背景移到了當代台灣的南投,輕鬆帶入卡拉OK、宅廢物、憤文青、中台關係等在地元素。劇中的大姊為了操持家務,不得不考慮出售已逝父親的賓士車、央求舊友協助檢視家中的基金投資,具體描繪中饋之事的一面;家中唯一的男孩子面臨遠赴中國工作的抉擇,即使心中有所抗拒,仍難以抵擋時代的潮流。改編的新劇將契訶夫對日常的細節捕捉,以及對現實的牢騷詠嘆,順利移植到台灣社會。
劇裡也反映了華人社會的重男輕女的觀念:長子認為賓士車是爸爸留給「我」,所以反對賣車,強化傳統男性中心的家庭觀。他對女友謊稱自己在家中工作開視訊會議,姊妹們還得幫他圓謊、維持體面,甚至妹妹表示要取代哥哥去武漢工作,也被姊姊們所阻擋,要她在台灣找工作就好。大姊被阻止在家中有決策權、女性被反對在職場上有更大的發展。
《遙遠的東方有一群鬼》則來自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群鬼》。作品抓住了原著的「神」,置換到台中一個富裕人家的「形」裡頭。原著的「神」談的是挪威典型中產階級家庭的偽善,和家庭成員間的相互折磨與精神摧殘。
而重寫的「遙遠東方」版本,闡述的則是由王梅君一家的生活,帶出風光的顯貴家庭背後的千瘡百孔。她的先生是外人中典型的成功人士,是個用善款幫助孤兒院的富商,私底下的他卻當著兒子面前與學校老師偷情。活在丈夫出軌陰影下的王梅君,轉而在鬼影幢幢的豪宅裡以愛之名控制兩個兒子。在這裡,人人都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在見不到光的屋子裡,日復一日過著例行卻雖生猶死的生活。
《遙遠》一劇剖析本土文化,聚焦在儒家思想扭曲價值觀和倫理,探討當代親密關係中的病態行為,精準地探討華人世界裡的人際和家庭規範,而這樣乘著「愛」的詛咒,無論我們認同與否,都無處可逃。
拒絕做「關我屁事」的作品

「重寫經典」系列的發想,起源於許哲彬在英國讀研究所的日子。當時的他在劇場文化繁盛的英國,開始質疑起台灣戲劇系研讀並重演的經典名作,自己讀的到底是「戲劇系」抑或「西方戲劇系」呢?人們會關切這些不合時宜的他國故事嗎?這些情節對台灣人的經驗世界而言,或許其實是沒意義的?
搬演莎士比亞或契訶夫這些台灣人其實根本就不認識的作家作品,內容自然就會與民眾形成隔閡,「我自己去看戲的時候,也會覺得說,為什麼要花一兩個小時在聽你講十九世紀的挪威發生什麼事情?」許哲彬並不諱言:「講白一點就是,我們在拒絕做『關我屁事』的東西,因為我們自己也不想要看這樣的演出。」
但倘若把經典依著年代和風氣等現實狀態,把不合時宜的名作改編成「二十一世紀台灣版」,要如何呈現給觀眾看見?甚至對我們的土地,產生什麼意義?許哲彬和簡莉穎談論過這些狀況,決定拿兩人共同喜好的契訶夫《三姊妹》進行重寫一個經典劇本的嘗試。
得到的回響是,讀過原著的人,以戲劇系學生和外文系學生居多。「我覺得很有趣的是,知道這些原著的觀眾,當然會抱著一種對比的心情來看,雖然有的人買單、有的人不買單。就曾經遇過觀眾反應,在契訶夫的原作裡,時間是重要元素,《三姊妹》的故事漫長,劇裡總共包含四幕。「但我們的三姊妹是獨幕劇,劇中只經歷兩小時而已,他們會覺得這件事情為什麼沒有改編進去。」反對的回饋並非壞事,而是讓劇團認知到,原來每個人會在意的事情都不一樣。
而當沒有先驗知識的觀眾來看,則會以為「這是一個原創作品」,沒有人發現改編自西方,翻譯腔或是文化隔閡好像成功被洗掉了,這令劇團感到心意意足,覺得自己好像真的做出了一個前所未見的產出。
「反正我直覺創作最重要的,就是要好玩、要有『好想趕快把它做出來跟觀眾分享』的那種感覺。」許哲彬笑著說道:「作品就是創作者的延伸,如果作者勉強而痛苦,作品也就不會開心到哪,接著觀眾一定也能感覺到那份痛苦。」無論任何形式的創作,只要在創作的過程中不愉悅,缺乏熱情和嚮往,作品就沒有足夠的特質與觀眾溝通。劇場藝術在台灣舉步維艱,四把椅子的作品仍總是大賣,大抵就是因為具備了這些在不言中的力量吧!
採訪側記
那天採訪完畢,有幸留下來和導演談了兩個小時的藝術、劇場、教育、政治、新聞、夢想種種議題;談夢想時,還獲得一段深入人心的金句:「如果你現在需要的是價格,我就做這個價格裡面還有價值的事情;如果你現在需要的是價值,我要在價值裡面看到我值多少價格。」從採訪到聊天,無論是知識到精神層面都獲益良多,在兵荒馬亂的成長路上,尚有餘裕獲得一個豐收飽滿的午後。
延伸閱讀
更多報導請看生命力新聞
當西方經典劇作 搬到二十一世紀的台灣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生命力新聞 on Medium, where people are continuing the conversation by highlighting and responding to this story.
新聞來源:輔大-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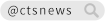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