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綜合報導 / 台北市
剛上小學不久,有一天我在放學回家的路上,遇到一個陌生男人發傳單,那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路人,不特別惹人提防的模樣。我們交會的時候,他抽起一張黑白印刷的傳單塞到我手上,叫我拿回家給大人看,我當時的讀寫能力只發展到注音,儘管勉強認出幾個「民主」、「人民」之類筆畫簡單的字,還是不足以拼湊出完整的句意,也猜不出傳單上說的是什麼。
回到家裡,店口碰巧沒有客人,只剩阿公一個人顧著,我把傳單遞給他,問他上面到底說的是什麼,阿公只瞄了一眼,就從藥櫃後面急急走出來,拽住我的手臂吼:「這會槍殺你知嘸知」
我當然嘸知,而且覺得手幾乎要被阿公拆下來。阿公兇起來很像暴力漫畫,阿嬤和爸爸的幾個兄弟姐妹,每一個都曾經警告我,阿公屬虎的,很兇。但是阿公真正對我這個寶貝孫女暴怒的次數,一隻手可以數完,這是其中一次。
我被吼得不敢作聲,阿公的意思是我會害自己或家裡的人被槍殺吧,是誰會來殺呢?有槍的人只有警察和阿兵哥,他們是保護人民的人,無端端的哪裡會殺我們?我不懂阿公到底在說什麼,路上天天有人拿傳單回家,無論想殺人的是誰,總不可能跑到這麼多人家裡,一個一個全部殺掉吧?
三叔也這樣被吼過。他還單身住在老家的時候,曾經提議大家一起上甲仙的錫安山走走,說朋友最近才去過,沒想過離我們這麼近的地方,有一個美得像仙境的世外桃源。我一聽到甲仙就想到芋冰,還沒來得及歡呼,先看到阿公的表情,趕緊把手腳和鼻息全都收斂得像隻烏龜,不敢嘁噌。
阿公對著三叔暴吼:「那種所在未使去!」說他不做正經事,專想一些「嘸屬賽欸代誌(不實在的事情)」。三叔很悶,平白被阿公罵了一頓,事後對著我抱怨阿公什麼都怕,才是嘸路用。我靜靜聽了,把錫安山這個地名記在心裡,判定那是個阿公覺得危險、但應該有點意思的地方。
很多年後,阿公老得不能出門了,我們終於上到錫安山,原來那是一個自外於社會的基督教會,開闢了一個山頭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當年為了土地等諸多議題,和政府有過多次激烈的衝突。我讀了停車場邊上控訴國民黨政府迫害的手寫海報,終於抓到一點蛛絲馬跡,能夠猜測阿公為什麼不讓我們來錫安山。衝突事件裡誰是誰非一時三刻很難看得明白,但是站在與政府對立的那一邊,似乎很容易有人流血。或許是因為這樣,阿公才以最高層級的戒心來提防,任何與政府為敵的人事物,他一絲一毫的邊也不許我們沾上。
我覺得阿公稍嫌誇張了,衝突抗爭難免有流血,但那畢竟是小眾之小眾,別人家的事,我們家安分營生,會有什麼事能輪到我們頭上呢,何至於要這樣怕?他對警察的忌憚根深柢固,經常拿警察恐嚇小孩,說他們會把不聽話的囝仔抓去關,我著實怕了許多年,要到上了小學,課本教我們軍人和警察都是保障我們生命安全的人,才漸漸放下心來,知道阿公只是嚇唬我。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那天凌晨,學生衝進行政院的隔天,坐在濟南路上的我,倒是出乎意料地又湊出幾塊阿公心中恐懼的拼圖。在學運過程裡,隨著社會事件的衝擊,多讀了台灣史料,我發現自己和阿公雖然在不同的時代,遇見不同的事件,卻很可能生出相同的害怕。
要說怕警察,我們怕的不是派出所裡面,點算到後來總會變成同學娟娟的爸爸,或菜市場文金嬸他家老三的那一種;而是在難見真身的雲霧裡,代表政府來界定暴民排除暴民的那種警察。一個凌晨的見聞讓我對國家和政府生出恐懼,我推想,阿公心中巨大的不安,靠的肯定不只是一個錫安山事件的餵養,能讓一個人怕到終身不提自己的害怕,那恐怕是更多更暗黑的見聞。
阿嬤熱中於婦女會的免費活動,我也愛哭愛跟路參加過幾次,在民眾服務站前面和村裡的阿嬸阿姨們集合,搭遊覽車出去玩。回來以後,阿嬤會說兩句某某民意代表人不錯,真慷慨,這次 了蓋歡喜,下個月選舉要「凳乎伊」(投他的票)的話。但阿公完全不會,他繳所有該繳的稅,履行一切公民義務,但是對於政治沒有一絲一毫個人見解。
每到選舉日,阿公出門投票前只會機械式地問過爸爸或阿嬤,應該投給誰比較好,沒有第二句話。爸爸還會說,做囝仔的時陣,曾經在門口看過軍用卡車上面載著用布條蒙眼的村民,不知道要去哪裡,有沒有回來。但是我和阿公相處的二十多年裡,沒有聽過阿公提起,他看過什麼樣的人,見識了什麼樣的場面。根據「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的原則,我好像不能主張,這個國家曾經驚嚇過阿公。
謎底後來是爸爸揭開的,在我追問之下,爸爸才模糊想起,大伯父從前在日本讀書,一次回國的時候,傻呼呼接受友人請託,幫帶了一份包裹,入境的時候被翻出一本《毛語錄》。阿公費了許多精神和金錢,才讓大伯父平安回到家,但警察從此時不時過來關切家裡的日常起居,讓阿公很難放心。我猜是那些我根本無從想像的周旋,讓阿公決心成為無聲的公民,安靜得彷彿什麼事情都沒發生過。只是,在那個時空背景下,他的沈默反而為自己打上一盞探照燈,成為我的歷史舞台上說出最多故事的那一個。
本文、圖由大塊文化出版公司提供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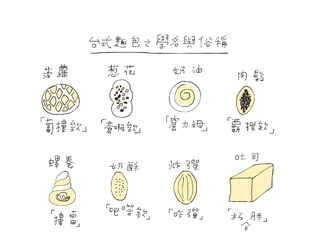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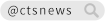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