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葉冠妤、靳詠雯/新北市報導】新冠疫情爆發,萬華十數間茶藝館調查出確診者的足跡,萬華一下上遍各大媒體版面,不僅被揶揄做毒窟,萬華居民更是備受歧視,好似只要是與萬華二字扯上關係,便像沾染新冠病毒。社會原先對於在茶藝館工作的性工作者本就持有異樣眼光,處在疫情風暴當中,他們身上撕不下的標籤更加固著,但是於此同時在萬華耕耘多年的曉劇場逆風發聲,在劇場YouTube頻道上傳於艋舺國際舞蹈節期間拍攝的紀錄剪輯,表示將與萬華在一起、挺過嚴峻疫情。
在北藝大埋下的種子與收穫的養分
鍾伯淵,畢業自臺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導演組,現任曉劇場藝術總監的他,二〇〇六年偕現在的藝術顧問李孟融、資深演員曾珮等人一同創立了曉劇場,以「想要來做自己的戲」為發跡,加上覺得單純只是做戲有些可惜,便決定成立了劇團。在北藝大就讀期間,他發現戲劇系的演出大多以西方劇場為主,從美國大蕭條時期的經濟狀況、歐洲的種族歧視到莎士比亞的戲劇等。「覺得有點虛浮,找不太到臺灣的影子。」所以曉劇場的作品內容多以在地題材作為創作核心,透過作品來反映現代社會議題。
「當我有些想法或意見,不是大家所認可的,我也不會害怕說出來。倘若我不是這樣認為的,我就會為我的想法發聲,如果你那樣認為請你發出你的聲音。」鍾伯淵說道,在北藝大的教育訓練當中,師長經常用如果的方式提問,像是如果你現在不去做這件事情,那你會去做什麼?這樣的教育方式創造出了更多彈性空間,讓學生勇於表達的同時,也因為保持懷疑、廣泛假設,所以在未來的路上面對波折的時候,更可以從容應對。

走進萬華,走近萬華
曉劇場二〇〇六年成立於北投,二〇〇九年受到房租調漲影響,從北投遷至萬華,但是他們一直到進駐萬華的第三年才連做了《擺渡艋舺》、《她獲得約翰的吻並成為胡立德的女人》兩部分別與街友、性工作者有關的作品。在此之前,他們有長達三年沒有做跟萬華有關的作品。
「我們意識到萬華的人其實很害怕被妖魔化、標籤化。」鍾伯淵解釋道,在二〇〇九年他們初搬到萬華的時候,劇場有做一個小戲,內容引用張曼娟老師的文字去訴說對生活與城市的故事,其中有提到他們剛來艋舺的第一印象。當時來觀戲的萬華社區大學的民眾對他們說:「我們來看你們會怎麼說我們萬華。」也因為這樣,他們決定花更長的時間去認識萬華,也在過程之中不停改變對萬華的想像。
「剛開始我們會囑咐成員排練時要成群結隊的離開,隨著時間過去發現其實很安全,從來沒有遇到過任何事情,即便忘記鎖排練場的門,也從來都沒有遭過小偷。」鍾伯淵說。
萬華三流:流民
紅及一時的電影「艋舺」於二〇一〇上映,以艋舺清水祖師廟角頭少年的視角,描述一九八〇年代艋舺地區幫派分子與少年的愛恨情仇,電影深植人心的同時也讓大眾對萬華三流:流民、流氓、流鶯中產生更加固著的既定印象。因此二〇一二年曉劇場決定深入街頭對街友與性工作者進行採訪,「我們希望可以了解為什麼他們會走到這一步,是在什麼樣的狀況下決定,又是怎麼繼續下去的」鍾伯淵說。但是礙於性工作者的取材不易,因此他們先從街友著手,以《擺渡艋舺》作為主題,開始為期半年田野調查。
從產生疑問到想像,曉劇場希望可以透過劇場將議題的不同面向打開給觀眾看,鍾伯淵表示:「我們在做作品的時候可能沒有一個很明確的答案,或是可能會有一個想像,但是在做作品的時候會發現其實好像不見得全然是如此。我覺得這是做劇場最有趣的地方。」而他所說的這種情況也完整體現在此部作品的製作當中。
在與街友實際接觸之後,鍾伯淵驚訝的發現街友的生活與一般人並沒有什麼不同。「我們可能會覺得街友就是一天到晚在喝酒的人、街友就是不工作的人,可是事實上很多街友他們早上七、八點就把他們的床整理好放在旁邊,跟著來找計日工的發包人去工作、舉牌子,很大一部分的人是早出晚歸的。」他分享其中一位街友魏先生的故事,魏先生作為緬甸難民,流亡到臺灣最後輾轉來到龍山寺成為街友,這也顛覆常人對於街友「本土」的認定。「這讓我們覺得,我們所有人都有可能會因為遇到一件事情,讓我們走上顛沛流離的生活。」鍾伯淵說。
除此之外他們也在邀請街友一同參與演出的這項決定中,更加堅定與人之間的信賴關係,「在一般演員身上都可能出現缺席甚至臨時退出的狀況,參與演出的街友大胖、小胖兩人都沒有手機,一直到演出前我們都會有這樣的擔憂,但是他們兩個沒有一次缺席排練。」除了感動中鍾伯淵也為先前的擔憂感到慚愧,思考要如何擺脫社會階級、地位跟對人的既定印象,大胖跟小胖給他們打了十足的強心針,「他們只是生不逢時,仍然值得被信任」。
《擺渡艋舺》最後以男孩變成北極熊的故事,呈現一個被北極熊養大的男孩最後真的變成北極熊與他的家人在一起,穿插街友們的故事表達,無論他的家人、他們是什麼樣的族群,有一天都可以在一起、可以做到一些事情。「我們希望觀眾在理智上觸發思考,不是讓觀眾來看完覺得很難過、很同情就結束了,而是讓他們去想像會不會有一個這樣的轉折,以至於我也走上同一條路,假設我可能也會因為這樣而選擇走上同一條路,那我現在還要不要批判它。」除此之外劇團也希望可以藉由這部作品讓街友找到力量跟勇氣,觀眾看著他們嘗試演出,他們也在演出後認定自己可以完成一件事情,回歸社會後去做他們原先沒有想像過可以做的事。
萬華三流:流鶯
「在與姐姐們的八個月的訪談中,前三個月都在碰壁。」相較起街友更為敏感的性工作者,曉劇場在取材上面耗費了相當大的時間跟精力,因為採取街頭攔截的方式,起初前往調查的女團員們一度被姐姐們誤以為是要去搶生意,也會碰上男客人上前詢價。但是在了解來意跟長時間的接觸之後,「姐姐們人都很好,會照顧我們的團員」鍾伯淵說。礙於性別,男性團員無法參與性工作者的訪談,因為本質上會被誤認為顧客、產生錯誤認知,「當她們知道我不是這樣看待她們的時候,她們其實會產生一種自己的羞愧感。」因此此部作品的田野調查,幾乎都是由女性團員來進行。
只有一次他與劇團行政顧問育伶和姐姐約好去到她的房間進行訪談,那一次他發現其實姐姐們不僅會閱讀,背後也都有自己的生活哲學,「因為當他們的生命在很困頓的狀況當中,反而會產生更多思考,順遂的人其實反而不太會思考生命的本質,愛與罪惡,姐姐們在這個過程當中,思考的深度其實反而超越很多人」鍾伯淵說。
最後《她獲得約翰的吻並成為胡立德的女人》這部講述性工作者的作品以一個妓女的房間呈現,描述一名妓女在閱讀沙特《可敬的娼妓》與《莎樂美》這兩個劇本,並來回穿所在其中,期待自己可以成為故事中的主角,像《莎樂美》一劇中的莎樂美,為了不被父王玷汙,在為父王演出了七層紗舞之後向父王要求要了約翰的頭,便當著希律王的面吻了約翰的頭顱,即便被處死也要堅守貞操,可惜她不是莎樂美,她僅是在她的房間中扮演著故事中的角色。「故事中,姐姐們也透過聲音演出,表達自己如何看待愛與生命,觀眾會在觀賞過程中聽到這段訪談,但是也因為姐姐們多少還是有所避諱,所以聲音都經過扭曲變聲。」
「他也是人、你也是人,我們都是人。或許你做了一個什麼樣的選擇或你出身在一個怎麼樣的狀態,你也會跟他一樣,我們處在的位階常常讓我們忘記這件事,劇場是為了要去喚醒這些東西。」鍾伯淵再次強調劇場是一個提出問題跟大家討論、透過故事讓大家重新思考,自己原先認定的想法或意見是不是有可能被鬆動的地方。
這兩部戲加起來便花費小劇場一年多的時間來進行田調,因為工作期程往往比一般劇場來說更長,所以曉劇場採團員制的方式運營,沒有固定成員,「我們希望在所有人都理解的狀況下我們再來進行創作,我們對於演員的需求不只是我來演演戲,而是他要真的跟這些人聊過、知道故事、開始有想法,然後回到劇本去思考怎麼樣演出。」
艋舺藝術舞蹈節 藝術的切入點
不只有戲劇演出,曉劇場同時也主辦了艋舺國際藝術舞蹈節,邀請數十個國內外團隊到萬華街頭進行舞蹈演出,「很多創作者跟我們常常是在學校、在書本上做角色功課,但是來到萬華之後我們是在街頭上做角色功課,希望延續這樣的感覺把創作者拉到萬華來,讓他們在這塊土地上找到他們的創作」鍾伯淵希望可以透過舞蹈這個較為強烈的藝術形式,吸引更多人駐足萬華,觀賞萬華特殊的建築以及人文景觀,同時也讓這個藝術節形成萬華特有的風景。
藝術節主題從第一年的「未完成」、第二年的「在一起」到第三年是跳躍的「躍」,鍾伯淵表示這三個名字是希望可以讓觀眾跟創作者知道這個舞蹈節不是要去做一個很完整的作品,也希望創作者不要有害怕被評價,認為這都是在完成作品的過程中很重要的養分,「我們希望場地跟觀眾、跟城市是融合在一起的,我們在製造的是如同萬華這種很緊密的人際關係。」除了利用街頭空間創造創作者跟觀眾的對話外,艋舺國際舞蹈節也是一個提供給創作者嘗試的平台,其中會聯合一些策展人、場館中心以及文化局,「有點像藝術交易市集」鍾伯淵說。
跟萬華站在疫起 共度難關
「外界對於萬華複雜的定義是因為萬華包容很多不同的人,當一個文化區域趨於劣勢的時候很容易被針對,但我們其實只是在獵巫,而不是在真的理解事情」針對先前爆發的萬華茶藝館事件,作為在地劇團,曉劇場也在自己的YouTube 頻道「曉劇場」放出艋舺國際舞蹈節的紀錄影片,表示將與萬華站在一起。
鍾伯淵說:「萬華在歷史上很多人都是靠自己出頭,因為以前的工作移到萬華,街友跟性工作者不受法律保護,也是自己在保護自己,在疫情爆發之時萬華所有的人很快便連結起來」不僅是早於政府之前自發性停止內用,萬華的地方議員跟商家更是迅速的就建立起外送、外帶名單,針對街友的日常照顧跟監控,萬華的社福單位也非常積極在處理、預備配套方式。
「萬華,華是蓮花、一萬朵蓮花,這裡是一個很漂亮的地方,這些花開在一片汙泥之上,汙泥可以開出很美麗的花,所以我們為什麼要害怕汙泥呢,事實上它可能可以孕育出更美麗的事情。」曉劇場於疫情期間仍不停止的舉辦線上讀劇、讀書會等活動,同時也正在規畫安排過內外藝術家進駐萬華,希望在疫情過後,除了艋舺國際舞蹈節外,還可以為萬華帶來更多餘的藝術形式,成為萬華的藝術中心。
更多報導請看生命力新聞
新聞來源:輔大-生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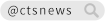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