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敏娟 採訪/撰稿 張書堯 攝影/剪輯 / 台北市
在台灣,有一群20歲以上,40歲以下的青年,他們在職場拚搏努力求生,卻依舊掉到「貧窮線」下。
大學剛畢業的七七,和男友一起在東華大學附近租屋,不只省房租,三餐也是能省則省。受訪個案七七說:「本來是想要做肉絲炒木耳,可是就省錢,我們就買薑炒木耳就好。我們會先看即期品區,因為它會打7折,因為收入不多嘛,就是要減少開銷,生活品質跟物慾也都是要減少。」
晚餐時間,兩人聊的日常瑣事,說的彷彿是自己的未來。還不到30歲的七七,畢業兩年,做過幾份工作都是臨時工。就業目標,她只鎖定短期的非典型工作。受訪個案七七說:「本來是在診所櫃檯打工,一天做4小時一個禮拜上4天的班,遊戲的陪玩或者是語音聊天,賺一點點額外的小錢。我大一的時候聽說,老師界已經飽和了,你想要進去學校當老師,還得塞紅包給校長,我就想說算了,這不是我要的生態。」
畢業於國立大學教育系,還沒進入到職場,就先聽說未來就業環境的黑暗,於是她放棄當老師,走自己的路。受訪個案七七說:「以目前來說就是非常勉強,然後沒辦法存到錢,比起過得很拮据,我根本沒辦法接受賣命工作的生活,如果那種生活才不是窮忙的話,我好像寧可選擇窮忙。」
存不了錢,也自認自己是窮忙青年,七七坦言從來沒有規劃自己的人生,考慮一輩子都不做正職工作,賺錢就辭職去旅行,沒錢再繼續找打工。
受訪個案七七說:「父母那一輩他們有嚐到甜頭,對我而言,我覺得我再怎麼努力,我都沒有辦法像我的父母那樣的成就,或者那樣的成功賺大錢,你只要願意努力,就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感覺。現在太多的變動性,金融海嘯、裁員失業風波、通貨膨脹,然後房價中國、兩岸關係等等,我會很害怕我就算努力了,然後也沒有一個好的成就,或是賺大錢。所以如果我就宣告我躺下來,就不是我的問題。」
七七的男友,明年即將從法律系畢業,對未來的人生,同樣感到希望渺茫。受訪個案瓜皮說:「應該說我肯定會是窮忙族,我不想要做那種,可能進公司普通的工作,我就是想當個創作者。像是我媽就會說,這樣子以後不穩定,要是到30歲還在打工怎麼辦,從來沒有想過未來會長什麼樣子。我覺得我現在,就有太多的問題要解決了,我沒有餘力去管那麼後期的事,我也不知道很多的報酬是什麼樣的,因為在我世界可能一小時時薪是170(元)呀,(貼圖)我從5月上架,到現在它們應該讓我賺了8千塊台幣。」
設計貼圖賺外快,其他時間,瓜皮寧願花在攝影上,在未來實現創作的夢。為了夢想,寧願當窮忙青年,在八九年級族群中很常見。受訪個案老宅說:「目前(工作)大部分是吉他彈唱比較多,那有時候會去當別人的樂手,可能是鼓手或者是鍵盤不一定。(工作)不太穩定,因為我們都是接活動,那平均大概2萬出頭吧。」
離開台南家鄉,來花蓮念大學工作至今10多年,30歲以上40歲未滿的老宅,堅持自己的表演理念,他只能從事兼職工作。受訪個案老宅說:「如果說我還想繼續做表演這件事情,那可能就不太適合去接正職的工作。像這個月我就沒有在那邊(酒吧)駐唱,就變成我要去找其他的工作,然後讓自己活下來。現在藥師助理這個工作,以我目前的階段來說,它的意義主要是在於「活下去」,可以活到2月,明年2月之後還不知道。」
就算生活隨時會斷炊,成為窮忙青年,這是老宅自願的選擇。受訪個案老宅說:「下班時間,還不能準時回家還要加班,你賺到的錢,其實好像也只能讓你,剛剛好地活下來,起碼我不用做這些事情,對現在生活狀態不能說滿意,但我接受它。如果說要檢討為什麼年輕人愛上班不上班,那也許可以反過來看一下,他們上班可以得到什麼。」
不想賣命,不談未來,崇尚自由,這彷彿反
台大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古允文說:「背後所隱藏的,剛好就是台灣整個勞動市場,到底是不是能夠滿足大家期待的問題了。越到現代社會你就會發覺到說,有時候並不是我們懶,有時候是社會上面,要找到適合的工作不太容易。發展太快了,你可以看AI一出來,說不定很多過去我們所習慣的,已經學習到的工作技能,說不定就會被AI所取代。這個勞動市場上面的年輕人,他不太能夠再像以前那樣,畢業了學的一技之長,我可以吃10年、20年、30年。」
記者徐敏娟說:「青貧窮忙族,幾乎成為新時代年輕人的代名詞,他們對於台灣社會環境的變動,以及國際局勢的不穩定性,感到力不從心。再加上不希望生活被工作給占據,因此他們寧願選擇活在當下。」
2002年,台灣每人每月實質經常性總薪資是3萬8千元,10年間增加到4萬1千元,成長7.8%。但消費者物價指數,2022年是負成長,更是近10年最大減幅,增加的薪資被通膨的物價吃掉,讓年輕人的體感貧窮更強烈。
蕭媽媽帶著兩個女兒,接受社福團體協助,住在台中租來的公寓,沒有固定工作,租菜園,偶爾靠賣菜為生。受訪個案蕭媽媽說:「我不想被人家看不起到處打工,只要有打工機會,我曾經一天兼3個工,你必須要去面對它,想辦法來處理它而不是來逃避它。」
生長在單親家庭的嘉嘉,半工半讀扛起家計。受訪個案嘉嘉說:「大學就要付書籍費那些,其實跟前面高中習慣的金額是完全不一樣,因為已經沒有政府的補助,所以就變成壓力是加倍上去。我現在大二,所以我現在就是盡量不拿家裡的錢,反而是給家裡錢的那一個,因為媽媽身體狀況不好,所以變成說我暑假放假去打工。」
正在就讀法律系的嘉嘉,在弱勢家庭中長大,目標是當上檢察官,為了改善家裡的經濟,她顧不了未來有什麼變化,只能奮力前進讓自己成功脫貧。台灣的貧窮定義,和許多國家都一樣,以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60%為最低生活費標準,一旦達不到就掉進貧窮線下。
全台灣的最低生活費是1萬3288元,每個縣市的貧窮線
因為《社會救助法》規定,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的標準,包含家庭人口和收入列計,把無聯繫的父母,或無實質扶養的子女都列入計算,這包括遺產和不動產,無收入者也全都預設為有虛擬收入,因此產生的貧窮黑數,通通被排除在外。
反觀歐盟,就業時數和機會不足,都是貧窮計算的因素。古允文說:「虛擬收入這個東西,是不是應該要取消,其實它有點是政府機關的方便,有工作能力,它就假設你有基本工資,所以它就不用去查證,造成台灣社會救助一種畸形的現象。社會救助太難進了,所以你好不容易進來的人,你不會想要離開,那不想離開的意思是,他脫離不了貧窮。」
貧窮線下,一張張辛酸無助的面孔,牽動人心,消除貧窮是世界各國懸而未決的難題,需要政府和社福團體協力扶助,接住下墜的人們,讓他們有勇氣為生活奮戰,搶救斷裂人生。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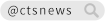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