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報導 / 台北市
期望在自由台灣落腳、重建自己的家園。下一段節目、我們繼續帶您來傾聽另一位流亡者的心聲。她是來自非洲烏干達的「茱麗葉」,因為女同性戀者身分、慘遭凌虐,而千里迢迢逃難到台灣來。茱麗葉、在台灣,是否能如願、重獲新生?
流亡者、離鄉背井、逃難到台灣,每個人都經歷過一段心酸的過往!像是來自非洲烏干達的女子、茱麗葉,只因為她是一位同性戀者,在家鄉、就慘遭性侵、並且被民眾丟擲石塊、凌虐,差點喪失寶貴的性命。而她的同性伴侶、則遭到殺害。為了逃離性別迫害,她飛越九千多公里、好不容易才逃來了台灣。一起來關心:台灣這塊自由的土壤,能不能讓茱麗葉、不再悲傷?
流亡詩人貝嶺:「對於華人,或是中國的難民來講,這是他們首選,台灣是最適合流亡者,或者難民,逗留的地方。」
流亡者茱麗葉:「這是我唯一的選擇,因為你知道當你要逃離迫害,當他們要殺你,你不能選擇想去的地方。」
流亡者龔與劍:「雖然過得很飄泊,很坎坷,所有我受的一些苦難的話,我覺得就是,在這個追求自由的過程中,我必須要承受的,我要付出的這些代價 。」
何處是家? 在台灣的流亡者
2014年2月,烏干達的報紙,竟刊登上百名, 同性戀者的姓名和照片,斗大的標題寫著「吊死他們」。流亡者茱麗葉:「在我的國家不能有同性戀,因為他們相信同性戀是不正常的,他們是撒旦,他們是邪惡的,他們有惡的靈魂。」
在非洲烏干達,2014年政府簽署反同性戀法案,原本打算判處死刑,但受到國際強力譴責後,
改判最高處無期徒刑,茱麗葉遭到社會集體的性別壓迫,欺壓者甚至是她的父母。茱麗葉:「在我很年輕的時候,大約15歲,他們把我賣給其他人,嫁給他。我才不會帶詛咒給他們,我才不會帶恥辱給他們,所以他們把我賣給一個,很老的男人,我嫁給他,結果我有了小孩。」茱莉葉有了3個孩子成熟懂事,目睹母親天天遭父親毆打,因此,她秘密計畫逃離,茱麗葉的同性伴侶認識台灣人 ,帶著孩子出逃時,卻遭遇民眾的「私刑正義」。茱麗葉:「他們舉發我們 我的另一半被殺了,所以我必須逃跑。
台權會法務主任王曦:「那她最嚴重的兩次,都是被一群街坊的暴徒,衝進家裡面痛毆,然後也有被性侵過。」
茱麗葉的就醫證明,正是她血淋淋的慘痛回憶。2016年她和孩子分離,跨越 9816 公里的距離,
從東非來到亞洲的台灣。但即便她逃過了死亡,在台灣這片異鄉,也要靠人權團體接濟,因為沒有難民法,4年來她只能靠簽證居留,規定無法工作,生活很難自立。
茱麗葉:「我希望台灣幫助我,讓我住在這裡,像其他人一樣生活,給我工作的機會,幫助我的家人,我的小孩,還有我自己。」
而同樣逃難來台的龔與劍,是中國的民運人士,重要的家當,僅有一個大背包,來得時候很匆忙。
龔與劍:「我就是靠台灣的一些個人的救助在比較,打個比方,就是比街友,比街友好一點點。
但是還是過得很冏的那種生活,只要等到中國大陸,有自由民主的一天,我立馬就回到中國大陸去。」龔與劍因為聲援六四購買禁書17歲時遭到中國政府,判處勞動教養兩年,被學校開除 ,
之後也無法工作,渴求自由的他,2015年以旅遊方式入台,已經滯留台灣4年,而追求自由的代價,是受盡和家人的分離之苦。
龔與劍:「感覺這些家人對家人的思念,是我們來到台灣之後,對我們這種精神的折磨最大的,有時候作夢,就夢到回到他們身邊了,真的是刻苦銘心,我們對不起他們。」
龔與劍時常評論兩岸,還有難民法議題,文章被各大報引用,而他也透露,曾經因為簽證過期,
只能躲躲藏藏,直到中華大學副教授曾建元,願意為他擔保,才能合法留在台灣。
曾建元:「非法入境台灣的,通常來講我們都要把他安置在收容所,就不能亂跑,那如果說有擔保人的話,他們就有所謂收容替代的制度,也就是說在這個擔保期間,他是可以自由外出。」
台權會法務王曦:「因為他不能合法工作,他就沒辦法自力更生,然後有的人可能運氣好,會遇到收容的人,可是有的他運氣不好,可能他真的會三餐不繼,那我們通常會轉介他社福單位或有食物的地方。」
這一天是龔與劍到移民署報到的日子,警衛警覺的, 不讓媒體拍攝,龔與劍是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收容替代處份,不能工作、艱困度日。
記者 林彥汝:「按照國際上的定義,所謂的難民,包含了無國籍還有外國籍的人士,而構成的要件前提,就是要跨越國境,而中港澳這三種身分,會觸及兩岸的敏感議題,也因為在這種特殊的政治歷史文化之下,遲遲無法通過的原因之一。」
在沒有難民法的情況下,台灣要如何庇護流亡者?外國籍或無國籍人士,只能適用《入出國及移民法》暫時居留台灣,而中國人要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申請,港澳人士則適用《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等於有三部法律體系處理,混亂的「難民庇護體制」獨步全球,但政府不得不謹慎 ,就是因為難民身份的真假,很難查核。
東吳大學法學教授胡博硯:「如果一旦有了這樣制度之後,可能會讓人,有些人啦,其實是以台灣,作為最終避難地點的選擇。你進來之後,你可能每年的業務量會上漲,基本上來講,你可能沒辦法處理,相關的問題。」
台灣關懷中國人權促進會理事長楊憲宏:「難民的議題本來就是一個困難,我們是兩公約的簽署國,兩公約簽屬的國家本身有個義務,就是通過難民法。我們不是可以依據依些狀況來判斷,是不是真實的難民,那他來了以後,對台灣是不是有幫助,這都可以列入難民審議,接受了以後 也可以重新否決。」
一邊擔心啟用難民法後 ,會引入不肖份子,而另一邊的民間團體,積極要求政府通過難民法
保障人權,兩方拉扯之下,流亡者該如何在台自立,仍舊無解。對已經有19年無法回到家鄉的流亡詩人貝嶺來說,他只能想辦法,對和他有同樣處境的人,伸出援手。
貝嶺:「這個房子就是我在今年4月底買下來的房子。」這棟房子空間寬敞,位在偏遠的烏來山區,還在裝潢階段,已經讓貝嶺感受到,很久沒有享受過的,家的味道。
貝嶺:「 原因就是我自己就是一個流亡者,我是直接從中國的監獄,直接送去美國的。對我來講 ,我太知道背景離鄉,我知道被驅逐或者逃亡的痛苦。我在美國住過不同的地方,我在台灣也不斷的遷徙。」
貝嶺是中國作家,2000年 他在北京私下出版文學人文雜誌,被控非法印刷罪 ,遭到逮捕入獄。
之後因為國際文學界的呼籲營救下,貝嶺獲得釋放,遣送美國獲得庇護,也取得護照,但他被中國政府驅逐,終生回不了家鄉。
貝嶺:「那就等於我失去了,跟我父母在中國見面的可能,那我父母年紀大了,他們也沒有時間到台灣來,這是一種悲劇吧。這也是一種不幸,可是這個世界上,有很多我這樣情況的人,我只能說這是一種命吧,命就是這樣。」貝嶺在泰國租下一間公寓,專門給各地的流亡者暫住,而在台灣,他也不吝提供處所,只是 由一個流亡者,收留另一個流亡者,終究不是長久之計。
貝嶺 :「那麼台灣社會其實對難民,可以寬容的、接受的,但是呢,人們又不認為,台灣社會目前形成一個,安置難民的共識。很多人仍然沒有辦法安置,我也蠻意外的,其實很多人權機構,
和人權組織,他們並沒有一個處所可以安排。」貝嶺在台灣完成他出版寫作的夢想,以過來人的經歷,協助流亡者,他的熱情 ,沒有被過去的苦難給磨光,而號稱民主堡壘的台灣,是否也有能力庇護,每一個尋求自由的靈魂。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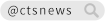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