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宜庭 採訪/撰稿 李宇承 羅哲超 攝影/剪輯 / 台北市
在監獄高牆內有一群人,他們的權益亟需各界重視,就是俗稱的監所管理員。他們是鐵窗內的執法者,與收容人朝夕相處,也身肩戒護與教化的責任。不過您知道嗎,其實他們的工作,高工時、高壓力、高風險。1名管理員,時常得面對上百位罪犯,心理壓力難以紓解,而以值夜班來說,工時更長達25個小時相當辛苦。監所管理員的心聲,與他們的勞動困境,帶您來關心。
早上8點,台北看守所的戒護人員統一集合,準備開啟一天繁忙的工作日常。報告科員四工場請示開封,開封指的是監所管理人員,帶領收容人離開舍房,前往工場做作業,這也是收容人一天的開始。穿過鐵門,我們看見高聳圍牆內,最真實的樣貌。謝銘鴻台北看守所主任管理員說:「因為我們要面對的是收容人,大大小小事情,都要由我們一手包辦,進來這份工作,你要先調適好自己的心態,就是說你是在幫助別人,甚至幫助一個家庭,讓他們回歸到正常的路。」
監所管理員,是犯罪矯正的第一線,華視新聞雜誌深入台北看守所,記錄下他們的日與夜。謝銘鴻說:「有些同學他們看診用藥,我們會眼同他口服下去,確保他有把藥吃下去,因為避免他有留藏藥的狀況。」
第四工場主管,41歲的主任管理員謝銘鴻,原本是補教老師,也曾在賣場當幹部,考上公職後,投入監所工作至今9年多。四工場以毒品犯為主,這天作業是紙袋加工,偌大的工場裡,1個人面對91位收容人,他得保持警戒,一刻都不容鬆懈。謝銘鴻說:「像我剛剛在巡視工場的時候,我還是會去聽有沒有在人講話,哪邊比較大聲,或是同學突然站起來,因為可能兩個人一言不合,他們就會吵架打架,就變成說你的心,是一直緊繃在那邊,一直懸在那邊,擔心著什麼時候會有事情發生。」
汪承漢台北看守所戒護科專員兼股長說:「我們這邊工場大概92或98人,那在像其他的大監,200人都有可能。但卻只有1個的工場主管坐在台前,其實那個心理的壓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因為暴行管教人員的狀況,並不是沒有發生過。」謝銘鴻說:「我會控制中間的門,帶著主管在前面那個門,我們會眼同戒護,看著他們出去,那再看著他們回來。」
矯正工作環境特殊,他們和形形色色的罪犯朝夕相處,除了防止收容人打架、自傷、違規,也得當心自己被攻擊,背負著無形的壓力與風險。謝銘鴻說:「印象中比較深刻的就是,在忠一舍有一個同學滋事,把他做壓制,那後來也是有受傷,也是有上法院,為了避免家人擔心,所以基本上我不會跟家人說。」賴擁連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系系主任說:「傳統以來因為監所,它必須要仰仗很多的戒護人力,做戒護管理的工作,第1個就是會變成勞力,那第2個就是勞心,任何一個管教不當,就會可能構成,收容人提起申訴陳情,還有訴訟的標的,就變成是內外煎熬。」
陳世達台北看守所主任管理員說:「比較嚴重的癌症,四肢比較殘缺,不能自理生活,或者是有大小便失禁的狀態,這些同學可能都必須,要先收容在這邊觀察療養。」他是陳世達,從事矯正工作12年,和另一名助勤人員,兩個人管理病舍,癌症、行動不便的收容人,都會住進這裡,目前共收容約80名中重症者,陳世達得負責他們,每天的例行看診。
陳世達說:「原本從事電子業,長官希望要派駐中國,我是不願意離家,所以我選擇考個公職,就進到這個職業來。」陳世達說:「在帶一個舍房其實並不簡單,就像我現在在病舍,我自己有點像一個保母,我們要更多的愛心跟耐心,來看他們的狀況,才不會衍生一些不必要的戒護事故。」
不同於其他公務員朝九晚五,監所工作分為日夜勤,夜勤人員必須從早上8點,上到隔天9點,整整25個小時,其中雖然穿插9個小時備勤,但仍得隨時待命。陳世達說:「夜勤會加班,最容易出現就是在大量的外醫,如果外醫急診就是一組人力,就必須要兩位戒護人員出去,勤務點比較遠,一定會超過25或26小時。」
值勤時間破碎、分段休息,讓他們難以獲得充足睡眠,工作環境受困在鐵窗內,有人難免感嘆,自己就像坐苦牢的人。汪承漢台北看守所戒護科專員兼股長說:「晚上6點之後就進入夜間模式,就是夜勤舍房同仁的執勤時間,像我們北所是分三三四四,就是上3小時休3小時,上4小時休4小時。」陳世達說:「每15分鐘必須要巡簽一次,如果說他取得一些工具,可能想要自傷自殘,就可能會利用在夜間,大家都熟睡的時候進行,那你在舍房動態,你就必須要每一房都很注意。」
監所宛如社會的縮影,監所管理員被稱為血汗公務員,勞心又勞力,是這群站在矯正前線,奉獻心力的執法者,最寫實的勞動困境,人力不足更是長期的沉痾宿疾。李宜庭記者說:「監獄人員,是犯罪矯正的最前線,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們面臨著高工時,高壓力以及高風險,我們現在的位置,在台北看守所,全所一共有344位監所人員,其中戒護人員261位,但收容人數就有2700多人,常常1位管理人員,就得面對上百位的收容人,這樣的情況該如何緩解。」
根據法務部矯正署統計,目前全台51個矯正機關,矯正人員預算員額有8800多人,但實際人數則為8300多人,缺額超過400人。賴擁連說:「2015年之前,管教人員被受刑人攻擊,案件數每一年,大概就10件20件左右,可是從2015年之後,就開始竄升了,40幾件、50幾件、70幾件。所以也反現在一個現象,我們的矯正人員離職率,2014年以前的時候,大概控制在百分之3以下,現在也跳躍到百分之6左右。」
而在全部的矯正人員中,戒護人員有5726人,以往收容人數超過6萬名,戒護比高達1:13,近兩年因為疫情衝擊,非急迫性的案件,各級司法機關大多暫緩執行,收容人數降到5萬1千多人,不過戒護比還是達到1:9,與其他國家相比,仍是相當高。詹麗雯矯正署簡任視察說:「香港的部分人力比是1:2,英國是1:3,美國跟日本可能都是1:5左右,那以我們現在最好的,人力比1:10左右,其實也跟他們的人力相差甚遠,人力的增補是我們,一直要去努力的目標。」賴擁連說:「如果是晚上的時候,可能是1:50或1:100,現在很多的同仁,特別是基層的,他管制6年之後,他馬上就找相關,可以對接的職務,他就請調出去了,這個對組織來講其實是不好的。」
監所管理工作,沒有超乎常人的毅力和抗壓性,實在做不來,許多人憑著一股熱忱和教化的使命,持續堅守崗位。謝銘鴻說:「一開始剛進來工作的時候,我很容易把負面情緒,帶回去家裡。我太太就跟我說,叫我不要把她當收容人,我從那個時候,我才慢慢去改我的調適的方式,跟我管理的模式,然後跟我家人應對的方式,我覺得這段時間,是最累的最痛苦的。」
陳世達台北看守所主任管理員說:「在從事這個工作,剛開始會有很多的不適應,夜間的輪值,那身體上面的負擔,都必須要自己去做一些調適。」詹麗雯矯正署簡任視察說:「收容人暴力攻擊,輕生逃脫的事件,難免會造成戒護人員心理的,一些壓力跟負擔,所以我們有所謂的,創傷後的症候群,我覺得最需要去照顧的,是我們第一線同仁的心理衛生的健康。女性的話,沒有辦法兼顧家庭,我覺得她們會比一般男性,更為弱勢。」
如何留住人才,解決人力窘境,專家建議開發科技協助,朝智慧監獄邁進。賴擁連說:「現在比較好的先進國家,他開始開發科技來協助,比方說新加坡甚至韓國,都開始用所謂的機器人,擔任這個巡邏的工作,我只要在中央台看著機器人,他巡邏時候的影像,我大概就知道受刑人的一舉一動,台灣現在也面臨到,要走向這一途。」
詹麗雯說:「嘉義看守所有智慧廊道,自動啟閉的一個門禁管制,那我們就可以減少提帶的時程,那對於我們同仁的負擔可以減少,可是為什麼只有去年嘉義看守所完成,因為經費非常的有限,希望就是說政府給足夠的經費,我們讓51個監所,都可以一起來用。」
合理的福利條件,轉變刑事政策思維也是關鍵。詹麗雯說:「警察的危險津貼,最低6千多元,第一級的可能是8千多元,我們的戒護人員,最高的也只有4千5百元,跟其他同類型的職類,我們確實是偏低,爭取是我們矯正署一直的責任,那我希望就是說,外界能夠一起重視這個問題。」
賴擁連說:「新的刑事政策的改變,或刑罰對犯罪人的改變,就是我們要親社會化。如果我們都認為說,關人犯很便宜,我的錢不用增加,你們這些都很耐操,我的人不用增加,但是你可以收那麼多人,就一直丟一直丟,那這樣子的一個刑事政策的,思維其實是不對的。」
汪承漢說:「某些團體可能重視,部分收容人的人權,這點我們都持肯定的態度。但是相對應的,我們是在第一線,在戒護執勤的同仁的權益,是不是也能夠,獲得相對等的一個提升。」監所管理員,直視外界痛惡的罪惡,也看過洗心革面的懺悔,他們或許是受刑人能夠改變的契機,卻也和過勞血汗畫上等號身負重擔,他們的權益亟需社會重視與改善,他們的付出,也需要更多尊重與肯定。
汪承漢說:「清道夫很辛苦,可是他掃地的時候,有人看得到,監所管理員很辛苦,可是社會看不到。我們隔著一個圍牆,其實要被看到不容易,我們不求像警察一樣能見度高,但是至少讓我們做的事情,能夠被社會肯定。」陳世達說:「選擇監所管理員這個工作,只要能夠影響少部分的人,走上正途,我就覺得很開心了。」謝銘鴻說:「如果可以多救一個人,出再犯輪迴的話,對我來講,就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就是我的價值的存在。」
生活在高牆內,和收容人看著同一片天空,監所管理員的甘苦,一般人難以體會,但也因為有他們,才能撐起台灣犯罪矯正,與改變社會的力量。看見血汗公務員的難為和處境,聽見他們的心聲與盼望,更能凝聚體制改革的動力。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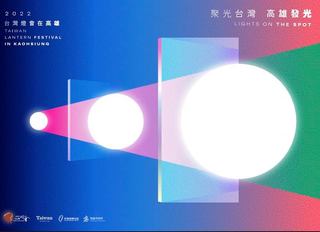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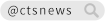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