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葉德聖 / 台北市
台中市政府爲迎接江陳會,預計規劃三萬坪抗議區,屆時看得到,聽得到,「就是打不到」。對此,曾為野草莓運動的發言人,現為東吳社工系講師的謝昇佑批評「台灣民主大開倒車」,並質疑「這是不是形同在那個框框裡,我們才擁有言論自由?」
謝昇佑認為,言論自由是憲法所賦予的基本人權,不管是在抗議區外或抗議區內,在任何地方都能夠發聲,「只有在保守的國家,才會做此防範。」如果擔心發生暴力行為或是偏激言論,這本來就是民主需要付出的社會成本,而且在法律上「我不能在行為之前就先預設立場」,但確實應該做好防護措施。
他也認為,如果真要做最有效的防範,或根本不讓這種行為發生,這是極權國家的優勢,既然是民主國家,「不是要去排除,而是設法提高公民水準。」
而回憶過去野草莓運動,他坦言,野草莓雖然不是很成熟的社會運動,但它卻打開了網路世界年輕人的想像,透過網路大力號召串聯,當時很多人不看好,甚至有人預測「活動不超過三天!」
「當時誰也沒想到,但活動就這樣下去了,第一天成立時就有網路高手,在現場架起Live實況,警方還並不知情,動手驅離學生群眾,這些情況完全被紀錄並當場放送出去,之後學生和群眾就湧進七百人左右,從行政院被驅趕後,來到自由廣場有人就已搭起棚子,民眾的物資也湧入了,大家一看到,心裡就很清楚,要全力拼下去」,謝昇佑回憶道。
去年十一月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期間,警政單位為因應不必要的抗議場面或衝突,行使路檢盤查、物資扣留,警方的驅趕行也引起爭議,也逮補了對會談表達不滿的異議人士,引起高度關注。在網路上,最早是由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李明璁在PTT2上發表在1106當天的行動和靜坐聲明,也要求總統和副總統必須道歉、警政署長及國安局長下台,最主要的是,立院必須修改「集會遊行法」。此舉立刻引發串連,在當時還有網友創作了一首《野莓之聲》抒發感受,而後學生就透過表決,以「野草莓」做為運動名稱。
在當時,真的關心集會遊行法的學生並不多,大部分的學生仍是對於政府動作和反志運動的宣洩,謝也坦承,「如果不是經過這個過程,也不會開始去著手了解集會遊行法。」但他們誰也不知道,參與的力量比他們想像的還踴躍,而自此之後,行政院也通過集會遊行法修正草案,許可制改成5日前報備,禁制區改設安全距離,限縮警察命令解散權,雖然努力推動的法案終於稍有成果,參與野草莓的學生仍認為現行集會法是「換湯不換藥」。
在那段組織期間,所有人雖然不認識,但是透過活動的發展,信任關係也開始建立,謝舉例到,「當時十二月七號那天,大遊行來了快要八千人,遊行前沒經過申請,我們自己做交通管制,在場來自個不同的單位、政黨,但是所有人拿的旗幟都是非常統一的,以學生的力量而言真的很不簡單。」
「只要自願,都可以來!」也因為這樣的特性,野草莓可以由此而生,但在激情過後,來自四面八方的內部成員逐漸面臨到背景歧異性的問題,參與野草莓活動而現為綠黨成員的李盈瑄就分析,後來人力精神隨著時間拉長漸漸耗損,而且因為這不是一個組織或團體,背景不同,自然很難再維持下去。
隨著學生陸續回歸校園,有的去當兵,有些則要趕論文,謝昇佑表示,某種意義上來說,透過傳播科技的發達、串聯,即便不成熟,「野草莓們」已寫了社會運動的新頁。
野草莓的逐漸散去,謝認為,「是可以預期的」,因為集會遊行法並不適合野草莓來推動,應交由像司法改革會、台灣人權促進會等專業兼具法律背景的團體持續進行。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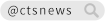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