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報導 / 台北市
今年是六四天安門事件30周年,對應天安門,台灣有自己的1989 ,有自己的躁動、有自己的衝突和迷惘,當然也有自己的勇敢、有自己的追求和期盼。舉例而言,1989,在台灣的電影史上就別具意義。
1989年,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奪下「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金獅獎」,這是第一部榮獲世界級三大影展的台灣電影。台灣解嚴之後,新電影出身的導演開始將觸角延伸到過去禁忌的題材,像《悲情城市》,就反映了台灣近代歷史的記憶。此後,台灣電影在創作題材上不再受到意識形態限制,一直延續到今天,都能享受多元、自由的創作環境。
導演魏德聖:「其實當時的我,基本上對社會無感、對自己躁動。可以說是只活在自己的世界。但我記得,1989年中國發生了六四事件,當時台灣社會到處都在講,校園裡也都在討論,發起募款聲援。當時我也在學校被『半強迫』地要捐錢。再來,我還記得很清楚的,就是台灣1990年,國民大會推選李登輝接任總統那天,我正在服兵役、原本正在桃園新竹一帶行軍測驗,突然被命令全副武裝、連夜急行軍回台北,一路上所有人都非常不安。不知道我們到底是要去保護新總統,還是要去武裝叛變。那天晚上心裡很害怕。」
回顧那個時期,台灣剛剛解嚴。很多社會運動,很多民眾都開始站出來,對抗政府體制。1989的台灣,在寧靜中、帶著躁動。躁動,是社會邁向民主、自由、開放、多元,所必然要付出的代價。而經歷過那個年代的您我,都有一段共同的記憶,那就是中國爆發的六四天安門事件。
為什麼當時在北京,有數十萬學生和民眾,佔領天安門廣場,示威遊行、靜坐絕食、要求民主改革?而為什麼一場學生運動,在1989年6月4日,會需要動用坦克車開上街頭、以武力鎮壓來收場?一起回顧三十年前,這場中國現代史上、規模最大、震驚國際的民主運動。
1989年4月15日,之前被迫辭去中共總書記一職,被視為改革開放的自由派人士胡耀邦猝逝,消息傳出幾個小時內,北京大學和其他大學學生便透過大小文字報,悼念胡耀邦,更表達對中國政治的不滿、對領導人的批評。當時就在北京大學創辦「民主沙龍」的學生王丹,也參與其中。
中國八九學運領袖王丹:「第一,當然就是要重新評價胡耀邦,我們當然也提出一些政治改革的訴求,包括言論自由、開放報禁等等。我們也提到一些經濟的,比如說提高知識分子待遇等等,大概就是七條訴求。」
4月22日,北京當局在人民大會堂為胡耀邦舉行國葬儀式,各大學學生突破天安門廣場的封鎖線。其中有人長跪遞交請願書,要求面見當時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更有學生與軍警推擠,遭到毆打受傷,開始醞釀發起全面性的罷課。
於是,427學生示威遊行如滾雪球般,匯集北京54所高校學生以及北京市民,超過10萬人直抵天安門廣場。示威學生:「我們罷課的目的,是要求政府領導人直接與學生對話。」
4月28日,學生成立「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由北京師範大學學生吾爾開希擔任主席。中國八九學運領袖吾爾開希:「我們給它簡稱是『北高聯』,北大、清華、人大、師大、法大、大專和大學加起來大概100多所。」為了應對這種局面,當時中國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就安排了所謂的「對話」,參與對話的學生這一邊,是由學校和共青團所組織起來的。原來官方的學生會等共青團代表,他們跟學運一點關係都沒有,這場對話當然是再一次激怒學生。
5月4日,學生再上街頭示威,這天正是五四運動屆滿70周年,10幾個小時的遊行,獲得北京市民以及天津、上海、成都等地學生聲援,加上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又對學運發表溫和談話,因此大部分學生樂觀地做出復課的決定。然而,中國高層始終沒有展開跟學生對話。
中國八九學運領袖王丹:「我們遊行、靜坐、示威、請願,什麼方式都嘗試過了,政府就是一點也不答應,我們當然只能使整個升級,我們只能用更激烈的手段,那就只剩下絕食了。」
中國八九學運領袖周鋒鎖:「事實上北高聯是試圖勸阻絕食,但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們沒有權利約束這些同學不要去絕食,最後有2千人絕食。我們有安排一條通道叫『生命線』,就是專門留給救護車通道,這些是完全靠一個一個人手拉手,日夜不停地站在那裡。」
5月15日到5月18日,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契夫訪中,意味著已矛盾分歧30年的中蘇關係恢復正常化,然而學生運動不但讓中蘇會談尷尬,也令中共高層臉面無光。
5月18日,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終於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絕食學生代表王丹及吾爾開希等人。中國國務院前總理李鵬:「我們北京這幾天已經陷入了
,可以說是一種無政府的狀態,我希望同學們想一想,最後會造成什麼樣的結果。」
中國八九學運領袖吾爾開希:「當時有一些媒體報導說,我的態度是否過於強悍,是否我們的立場強悍,刺激了共產黨。一方面我沒有強悍,我當時作為學生代表表達的所有的立場,都是我非表達不可的立場。」
中國八九學運領袖王丹:「我們當然知道不會是多好的結果,以為最差的就是
運動沒有取得成果,然後我們回到學校以後,這些學生領袖、這些學生組織者一一被開除學籍,甚至被捕的可能性,我們都想過,但是用正規軍開槍,這完全沒有想過。其實當時在黨內保守派勢力,在鄧小平的支持下,已經決定要鎮壓了,所以他(李鵬)態度當然強硬了。」
至於反對武力鎮壓學運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在5月19日,公開向天安門廣場學生呼籲,盡快結束絕食之後,便黯然辭職。
中共當局決定在5月20日,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超過25萬名學生與群眾
無視於大軍壓境的威脅,持續集結、圍堵軍車進入,然而,山雨欲來,一觸即發的緊張態勢,讓天安門廣場學生陷入了「繼續占領」與「撤離廣場」的觀點分歧。
中國八九學運領袖王丹:「我是主張撤出廣場的,這是一個很多人會去追究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沒有撤出廣場?但如果實事求是地講,在當時的情況下不可能撤出廣場,你可以想像這種情況,就算99%的人真的要撤,然後只要1%的人不走,那99%能撤得了嗎?」
中國八九學運領袖周鋒鎖:「天安門廣場堅持的學生,也有他堅持的道理,因為中共已經顯示了,他要軍隊鎮壓的那種情況下,離開天安門廣場就是分散了這種力量,當時堅守在那裡的人就是希望,要等待6月22日的時候,開緊急人大。」
只是,來不及等到全國人大舉行緊急會議,中共最高決策層早已調軍布局,決定武力鎮壓。
1989年6月3日下午,戒嚴部隊第38集團軍的先遣隊伍,被民眾圍困在天安門廣場西側,軍民對峙數小時,情勢緊張。晚間,各路大軍朝向天安門廣場進發,遭到民眾和各種路障堵截,軍隊開槍了。
中國六四事件親歷者、時任中國政法大學教師吳仁華:「最早開槍的是38集團軍的部隊,第一個六四死難者宋曉明,就是在6月3日晚上10點鐘左右,在西長安街的延長線、五棵松路口的人行道上,中槍死亡的。」
第38集團軍沿著西長安街向天安門廣場開進時,經過木樨地和西單路口一帶,這個區域遭軍隊射殺輾壓死傷的人數最多。中國六四事件親歷者、時任中國政法大學教師吳仁華:「第二個死傷比較多的,也是主要的屠殺區域。這是空降兵第15軍從南向北,向天安門廣場進軍時,經過天橋珠市口前門一帶時,就開槍屠殺民眾跟學生。」
吳仁華當時是中國政法大學教師,帶領學生擔任特別糾察隊,堅守在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下。中國六四事件親歷者、時任中國政法大學教師吳仁華:「在6月4日淩晨1點25分,空降兵第15軍就抵達天安門廣場的南面。在6月4日淩晨1點30分的時候,第38集團軍的部隊抵達天安門廣場的北面,也就是天安門城樓前面。所以從這個時候開始,他們就對天安門廣場進行了武力的清場。」
天安門城樓東側南池子街南口,38集團軍布置警戒線,但仍有不少民眾企圖衝入廣場,聲援堅守到底的學生。軍隊一次又一次開槍掃射,也造成了大規模傷亡。中國六四事件親歷者、時任中國政法大學教師吳仁華:「在6月4日淩晨3點過後,4個絕食請願的知識分子,劉曉波、侯德健、高新、周舵,就是決定出面跟戒嚴部隊談判,留出一條安全的通道,讓堅守的學生隊伍撤走。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包括,總指揮柴玲、副總指揮李錄、封從德,當時學生領袖不同意,不同意去跟戒嚴部隊談判,不同意主動地撤離。」
6月4日,約莫凌晨4點鐘,天安門廣場突然全面熄燈,戒嚴部隊發動最後清場。裝甲車和坦克車一路推進,輾壓學生帳篷,民主女神像轟然倒下,歷經最黑暗的半個小時,廣場燈光才又重新亮起。中國六四事件親歷者、時為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政:「就有士兵突擊隊,荷槍實彈的士兵突擊隊,突破過我們這些靜坐的學生,衝上了紀念碑,開槍把指揮部的喇叭給打掉,然後用槍托、用木棒毆打學生。最後指揮部跟戒嚴部隊,達成了一個協議,允許學生減少傷亡,最後從紀念碑座東南角撤出。」
方政當時是北京體育學院學生,6月4日清晨6點鐘,跟著同學隊伍沿著西長安街撤離。然而,行經六部口,突然後方傳出巨大的爆炸聲。中國六四事件親歷者、時為北京體育學院學生方政:「事後我們知道,這個爆炸物是毒氣彈,黃綠色的濃煙就把我們給籠罩了。就在我側身的這個時候,我就已經能看到,坦克車已經到了跟前,速度非常快。坦克車的履帶絞住了褲子跟腿,它就拖行、把你撕扯,撕扯了一段以後、拖行了一段以後,我才掉落下來滾到了路邊。」
中國六四事件親歷者、時任中國政法大學教師吳仁華:「編號106號的坦克是掉頭衝入路邊學生隊伍,當場造成11名學生死亡,很多學生受傷。其中有5具學生的遺體,送到了我任教的中國政法大學,我們就跪在5具的學生遺體面前,
所以我當時就一邊哭、一邊發誓,永不遺忘、永不遺忘。這也許就是我這麼多年,為什麼要去記錄六四屠殺的事實。」
1989年6月5日,在北京長安街上,以血肉之軀阻擋坦克車隊前進的青年撼動了全世界。媒體報導稱呼他「王維林」,卻沒人知道他確切的姓名身分,事後他音訊全無,至今生死未卜。天安門廣場、北京市區街道滿目瘡痍,軍隊忙著清理,卻無法抹滅民眾悲憤,無法平息舉世譴責。然而中國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先是對外宣稱,軍人加上民眾死亡將近300人,爾後,卻又反口不認。
中國國務院前發言人袁木:「在天安門廣場清理的時候,沒有發生任何的傷亡事故,沒有發生任何的傷亡,沒有打死一個人,解放軍的軍車,也沒有壓死過一個人。」
中國前六四戒嚴部隊軍官李曉明:「6月3日,我們接到了戒嚴總指揮部的命令,就是說要『不惜一切代價』,準時到天門廣場集合。」李曉明當時任39軍116師高炮團一營二連的雷達站站長,因為師長許峰消極不回應挺進天安門廣場的命令,李曉明才免於成為六四鎮壓的劊子手。中國前四戒嚴部隊軍官李曉明:「像有些軍官,他理解『不惜一切代價』,那我就可以殺人開槍,關鍵就是看你部隊的指揮官,看他們怎麼理解這個命令。」
根據中共統計,六四鎮壓事件共計有15名戒嚴部隊軍人和武裝警察部隊官兵死亡,而被授予「共和國衛士」的榮譽稱號,指稱他們都是死於「暴徒」之手。中國六四事件親歷者、時任中國政法大學教師吳仁華:「中國官方後來一再說反革命暴亂,所以戒嚴部隊才不得不開槍自衛、不得不開槍鎮壓,這是把時間先後因果關係顛倒了。這15名軍人,沒有一個死亡時間是早於1989年6月4日
凌晨1點鐘的,可是我們大家都知道,包括當年媒體的報導,屠殺是發生在1989年6月3日晚上10點鐘,戒嚴部隊開槍殺人在先,部分被屠殺所激怒的民眾
以暴制暴在後。其中只有7個人是被以暴制暴的民眾殺死的。」
中國八九學運領袖周鋒鎖:「當時在木樨地,因為我回到清華大學要路過那裡,我就去復興醫院去看。就是在一個自行車棚的地上,堆了40多具屍體,被白布裹著。」周鋒鎖名列學生領袖通緝名單第5,事發9天後被捕入獄。通緝令上的王丹、吾爾開希、柴玲、封從德等人也因為中共大肆搜捕行動,或被捕入獄,或流亡海外。
六四事件的倖存者就此背負歷史重擔,人民也在恐懼與監控中,從此噤聲。然而八九民運卻深深影響了鄰近的香港跟台灣,牽動著台港中的民主之路。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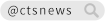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