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璽鈞 李宜庭 張書堯 張書銘 李宇承 / 台北市
在台灣,新住民人數、突破 54萬人,其中、來自越南的新住民朋友,就有多達10萬5千人,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早就已經成為我們熟悉的街坊鄰居,但您還記得嗎?1990年代,當部分民眾稱呼她們是「外籍新娘」時,語氣中總不免帶著歧視。
語言文化的隔閡、以及經濟的弱勢,讓不少嫁來台灣的越南新住民,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如今30年過去了,華視新聞團隊深入不同的家庭,帶您來了解新住民朋友們的困境、是否翻轉了?她們和台灣社會的那道鴻溝、徹底消失了嗎?一起來關心。
一大早傳統市場裡,有個嬌小身影穿梭其中,她是越南新住民,43歲的武氏釵,2010年她來台工作,3年後成為台灣媳婦,從此落地生根,現在開了家小吃店,每天親自採買。
內政部移民署的最新數據,台灣婚姻移民人數,突破54萬人,新住民成為台灣第五大族群,其中有超過15萬人,來自東南亞國家。
10坪不到的小小店面,是武氏釵和丈夫陳偉宏,實現夢想的地方,就連高齡90歲的阿公,都常來店裡幫忙,一家人共同打拚,攢出更美好的未來。
武氏釵:「越南新住民,辛苦是辛苦,可是為了未來還有家人要努力。」
孩子唸起越南童謠,也勾起武氏釵對家鄉的回憶,翻開照片思鄉情緒瞬間爆發,眼淚潰堤。
越南新住民 武氏釵:「大概多久會通一次電話?有時候一個禮拜,有時候好幾個月,一般大家都會把爸爸媽媽的照片放在身邊,越放會越想好不好,所以就不敢放太多,對,不敢放,一想就流眼淚。」
想辦身分證短期無法出境,加上開店賺錢沒能休息,武氏釵已經超過3年沒回越南,故鄉親人是她拋不下的牽絆,但想融入台灣,她們得比別人更堅強。
熟稔地打理自助餐店,她是嫁來台灣17年的阮氏金年,21歲那年正值花樣年華,卻成了家裡的經濟支柱,必須四處打工賺錢,最後憑著一己之力,6年前頂下店面,自己當老闆。
客人無心說出的「新娘」,曾經是無數新住民心中的痛!1990年代,來自東南亞和中國的女性,透過婚姻移民到台灣,人數逐年增加,她們的台灣丈夫大多是工農階級,甚至處於經濟困境,「外籍新娘」成了她們的「代號」,撕不掉的污名標籤。
越南新住民 阮氏金年:「(有的人)他會講說外勞那種,有時候會跟他講,我就說我們是台灣媳婦,那樣講就好了,再選擇一次妳還會嫁到台灣嗎?不要,怎麼說?如果回頭的話,我不想嫁來台灣。」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夏曉鵑:「那個時候所有的人,從官方甚至到學者學界的研究,非官方組織老師媒體都在講外籍新娘素質差,然後他們的孩子發展遲緩,那個素質的論述其實是一個非常明顯的階級主義,名稱這個習慣的用語,代表著一個社會的意識形態,所以它必需有一種社會的發動,去反省這件事情。」
長期投入新住民議題研究,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教授夏曉鵑,2003年成立南洋台灣姊妹會,發起正名運動,經過20多年努力,台灣對婚姻移民女性的稱呼,從「外籍新娘」、「外籍配偶」,改為「新移民」到如今的「新住民」,她們在台灣的處境逐漸改善。但除了歧視標籤,更早期來的新住民女性,歷經過更多的苦難和心酸。
50歲的林玉婕,是這家美甲店的主人,25歲嫁來台灣,已經在這塊土地過了一半的人生,但初到台灣時,其實有一段慘痛過去。
越南新住民 林玉婕:「當初嫁來是在南投竹山 ,那個時候我知道只是3個越南人而已,我最怕是語言不通,大家指指點點 ,覺得有點好害怕 ,到底是我們哪裡不對,還是怎麼樣,所以會擔心。」
80年代的台灣農村,對於這張美麗的外國臉孔充滿好奇,但語言的隔閡和文化差異,不時造成誤解,也讓林玉婕的身心備受衝擊。
越南新住民 林玉婕:「從小你長大就在那邊,突然變一個地方,你真的沒辦法接受,不會沒辦法想像為什麼,一下子我全部都沒有,朋友也沒有,親戚沒有,連個語言都沒有了,我每次去那個樓上曬衣服 ,我看到那個後山,我都會哭。」
獨自在異鄉忍受孤獨,以淚洗面的日子過了8年,搬到城市後投入職場,身分更遭來差別待遇。
越南新住民 林玉婕:「我沒辦法去做什麼更好的,只能做一些勞力的工作,被老闆娘她有一點小欺負我,因為她認為我是新移民來,我的工作可能會比人家多,然後薪水又比較少。」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夏曉鵑:「以前她們是連工作權都沒有 ,所以大部分是打黑工,有些雇主也許是他不知道,以為法沒有修,也許是故意隱瞞,他會告訴這個移民說,因為妳沒有拿到身分證,妳的薪資會比較低,妳沒有什麼福利這樣子。」
2017年發行的「我並不想流浪」專輯,道出許多新住民的心聲,洪金枝包辦了其中兩首,身為越南華僑的她,13年前搬到台灣定居,現在是小學的越南語老師。新住民的身分認同,曾是她難以解開的心結。
越南新住民 洪金枝:「我不知道台灣這個社會對越南這個字好像瘟疫還是流感的感覺 ,就是在我那個13年前的年代,感覺到開始我們在這個土地上 究竟是處著什麼樣的一個角色?然後我究竟在這個土地上,我擁有什麼樣的一個權利?」
當時的淚已流乾,但說到被歧視的心境仍憤憤不平,長期遭到不平等對待,許多姐妹開始參與公民運動,為新住民大聲爭取權益。來台19年成為台灣第一位,新住民紀錄片導演的阮金紅,也是成員之一。
新住民紀錄片導演 阮金紅:「以前可能是有比較姐妹比較對自己沒有自信,然後也沒有出來學習,或是跟台灣的朋友交朋友之類認識,所以就是這5年來就很多姐妹有這樣子一個膽量,可以出來推廣自己的文化。」
越南新住民 洪金枝:「(當年)越南的4所大學畢業的才能認證,越南這麼大幾百所大學,那要怎麼去認證學歷,所以那時候我去工作連高中的同等學歷都沒有的那一種。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夏曉鵑:「其實是會增加對台灣的不滿,就是覺得為什麼我跟你,我能力不比你差,可是我永遠都只是在當副手這樣子,或者是說我可能就是只能做這個很低階的工作,然後我被質疑這樣子。」
立法委員 林麗蟬:「這群人才她是嫁到台灣來,她是落地生根在台灣又有下一代,如果她是人才,我們何不接受她?其實我覺得這些是我們未來要更去努力的。」
近年來政府力推新南向政策讓新住民逐漸受到重視,但30年的鴻溝真的消失了嗎?在社會系統中,新住民仍常因為相關法令的缺漏,求助無門歷程坎坷。
立法委員 林麗蟬:「其實新住民相關的政策、相關的工作都落在不同部會,我在2年前就提出一個新住民的基本法,這些人的權益,你應該都要去做一些保障。」
內政部移民署移民事務組科長 楊金滿:「政府就是在104年成立行政院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這個層級就是提高到一個跨部會的層級,那在針對部會或者是地方,在推動新住民相關的服務的部分,可以透過這個平台提供相關新住民一個整合資源的協助。」
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夏曉鵑:「每次我們去陳情的時候,就說好啦好啦,我們個案處理,(行政人員)他們永遠會說第一個很麻煩,我們現在開放了,那就會有一些不法之徒會偷溜進來,所以我們都要把你當犯人來對待嗎?反過來想如果我是放到我們台灣人身上,它到底合不合理?如果合理我們再說,就是明顯不合理,為什麼就是講不通。」
穿上越南國服奧黛,每個姐妹笑得自信溫柔,人生的種種難題,也煙消雲散,我們看見新住民對生命的靭性,她們吃足異鄉之苦,熬過口音差異的歧視與偏見,靠著自己的力量,翻轉人生、過得「越」來「越」好。
透過鏡頭,訴說四位異國新住民姐妹嫁到台灣後,歷經破碎婚姻、不為人知的故事。這是入圍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的「失婚記」精彩片段。紀錄片導演阮金紅,拿起攝影機拍出失落一角,替姐妹與移工發聲。因為11年前,她同樣歷經一場失婚風暴,寶島一度成了地獄之牢,阮金紅忍受了8年,最後帶著女兒,勇敢結束噩夢婚姻。
新住民紀錄片導演 阮金紅:「他上班到晚上十二點才回來,之後我才知道他是去賭博,去玩女人什麼的一大堆,一旦你知道的時候,真的是已經後悔都來不及了,(還會動手是不是),對啊,他會家暴,賭博回來,今天你贏了是不是心情很好,可是你輸了是不是你也會生氣,所以他就會甩到我們這邊啊,跟我女兒這樣,就是我覺得我沒有得到夫家這邊的疼愛,我覺得我還滿委屈,因為我覺得我是一個單純、很善良的一個媳婦,也不是說不了解台灣的文化,只是我沒有機會去了解。」
走出空手無援的低潮過往,如今的阮金紅獨立且自信,而幫助她展開新人生,並讓她愛上攝影的,是她現任丈夫、知名紀錄片導演蔡崇隆。
新住民紀錄片導演 阮金紅:「其實我自己也懷疑我自己,我覺得我小時候才讀國小五年級耶,我到現在我能做這樣的事情,很重要的是我現在的老公就很幫忙很支持,不管是你做成功失敗,他都會鼓勵。」
儘管人生峰迴路轉,阮金紅不曾失去信心與希望,更特地在嘉義打造「越在嘉文化棧」,提供姐妹跟移工交流空間,更是他們在台灣,共同的家。
新住民紀錄片導演 阮金紅:「越在嘉是沒有在分你我他的,對,就是有時候,就是我們的移工也好,我們的新二代也好,或是我們的姐妹可能是因為遇到家暴啦,然後姐妹沒有地方住,那我們就會暫時給她們,就是做一個庇護這樣子。」
對新住民而言,家鄉難以遺忘,但在這片土地上有了家、有了孩子,根也就留在台灣。飛越海洋後的此岸人生,她們翻轉困境、綻放美麗!但反觀台灣,仍得透過更完善的法規、更友善的社會環境,才能保障新住民,讓她們不再流淚,在台灣寫出生命新篇章。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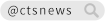


讀者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