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展瓏 文楷誠 施幼偉 / 台中市
位在台中的一所國中日前發生了重大的校園霸凌事件,一名國中男生長期遭到班上同學辱罵、嘲笑他的性向,他曾經向師長發出求救訊號,卻遭到漠視,因為不堪霸凌、一度輕生,所幸及時被從鬼門關前搶救回來!根據兒福聯盟調查,全台灣的國中學生,高達七成,曾經是校園霸凌事件的加害人、被害人,或曾親眼目睹。但真正通報到教育部的實際數字,每年卻只有一百多件。面對「校園之惡」,孩子們該如何為自己發聲?大人們又該如何改善校園霸凌的亂象?
雙腳架滿固定架,痛苦躺在病床上的是今年才國三的男學生,2019年4月22號,他從學校四樓墜樓,雙腳開放性骨折、脊椎受傷甚至摔到腳踝變形,緊急開刀才撿回一命。
國中生母親 (2019.4.25):「腳都沒有辦法,以後可能都不知道能不能站,這都不知道,當下我們真的是沒有辦法做任何的回應,我就只希望孩子能夠活下去,這樣而已。」
母親見到孩子殘破的身軀,哭到泣不成聲,原來個性溫和、長相斯文的他,上了國中後長期遭到同班三名同學霸凌,多次惡作劇,嘲諷他的外型,儘管他不只一次向班導師發出求救訊號,但情況始終沒得到改善,最後選擇輕生。
國中生母親 (2019.4.25):「我覺得他們真的很過分,我從來不知道他們說我兒子,說我兒子是同性戀,我很難過,因為他沒有跟我反應過。」
直到事發前幾天,男學生才忍不住向家人透露他遭到霸凌,只是家長打電話給班導,她不僅沒接,事後還跟孩子說無法處理,發生憾事後,校長更希望學生父母把「霸凌」改成「意外」,家長難以接受。
國中生母親 (2019.4.25):「校長就說,學生要申請醫療理賠,用「罷凌」會申請不到理賠金,我就覺得我孩子都還沒有,你就跟我講這個,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他要我們用意外這樣的方式去處理。」
班導師 (2019.4.26):「先安撫他的情緒,次數有多了之後,於是我開始當著全班的面,做了一個團體的輔導,我覺得,沒有什麼事情他必須要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
校方坦承,老師在聽聞孩子遭霸凌時,敏銳度不夠、沒發現問題嚴重性,事發後也隨即成立了「防制霸凌因應小組」,並向教育局通報,只是釀成遺憾,一切都難已晚回。而這樣的校園霸凌事件,其實從未停息。
2015年身形瘦小的陳虹約,勇敢站在高中校門口,舉標語反霸凌,用行動捍衛自己的權益,抗議高中三年一千多個日子,沒有一天得到安寧,他曾天真以為容忍情況就會改善,但沉默 卻讓噩夢持續上演。
陳虹約 霸凌受害學生 (2015.07.25) :「一個人講說下課去架陳虹約,然後下課其他人就是也會過來,譬如說一年級會有人就是掐我胸部然後轉,我就算講了也沒有什麼用,因為其實班上還有一些人是被言語罷凌的,其實老師知道,我覺得老師的處理讓我不會覺得想跟老師講,這種霸凌事件有很多人是不敢說的,因為我認為是在學校,大家會認為這是在好玩,甚至是大家不覺得嚴重性,甚至已經被霸凌了他們也不覺得自己被霸凌,可是那些傷害卻一直在累積,原來我高三面對這些情緒,我已經爆掉了。」
校方處理反應消極,調查結論是同學不是「性霸凌」、只是「性騷擾」,陳虹約選擇在畢業前夕站出來自力救濟,有人聲援,也有人選擇忽視,小蝦米對抗大鯨魚,只希望變調的青春畫上句點。但一個陳虹約走出來了,卻還有數千數萬個孩子蜷縮在陰影處,遭受校園霸凌的折磨。
翻開校園霸凌事件簿,一篇篇都是孩子們的真實血淚,兒福聯盟2018年針對全台灣11到14歲的孩子進行調查,發現近7成(66.5%)孩子有校園霸凌的經驗,人數高達56萬人,就有一成七的孩子在調查期間的兩個月內曾被霸凌,等於有超過14萬的學童活在恐懼和威脅之下,近一成的孩子遭遇霸凌、卻也霸凌別人,而超過六成四的孩子,是所謂的旁觀者,眼睜睜看著別人被霸凌,卻不敢出來發聲。
被霸凌過的孩子,大多數長大後陰影仍舊揮之不去。他們有的極度缺乏安全感,被黑暗深深籠罩,有的更差點走上報復社會的不歸路。像今年33歲的阿松,從小個性孤僻、不太懂得與人相處,加上口音關係,言語霸凌在他的求學過程中不斷發生。高二時,他情緒失控反擊,還差點鬧出社會案件。
霸凌受害者 阿松:「剛好因為我跟幾個交情比較好的同學可能剛好在聊天過程中有給他聽到過,提到說我怕高這件事情,結果剛好給他看到我靠在女兒牆那邊,後來把我腳舉起來,我差點摔下樓,他還不曉得事來由說,哈你會怕喔,我當下整個抓狂把他人往外面壓,旁邊人知道不對一直有在拉我,看到不對趕快把他拉回來,他那時候是真的整個人被壓在下面,我手一放沒有人過來,他就整個人掉下去了,言語霸凌對我而言算是一種精神上的一種壓迫,對於過去來說,我覺得是精神上的一種霸凌,你不知道對方什麼時候會想到一些 羞辱性的言語來攻擊你,就他不是肢體上面接觸的壓力,身體上面的講難聽一點你只是痛過就算了,精神上的壓力是你一直會想說為什麼人家要講這種話來攻擊你會讓你一直在腦海是散不掉的。」
讓他最印象深刻的是,國中時的好朋友,也是因為長期被霸凌,最後選擇加入幫派,也成了霸凌別人的加害者。
霸凌受害者 阿松:「他還被人曾經脫褲子、脫內褲、全身扒光、逼他在教室走廊上裸奔到這種程度,我的那位好朋友是被逼到那種程度,後來是霸凌最嚴重的那幾個,最後是被迫轉學,但轉學沒有用啊,你走了一個霸凌者會有其他人接力,他經歷過霸凌的事情,沒想到要去怎樣幫助別人不被霸凌,他想到的是加入一些可以讓他拳頭變大的人,跟著那些拳頭變大的人去霸凌曾經霸凌過他的人,霸凌你不當下設法解決問題,弄到被霸凌的人,如果說他要反擊起來那是很可怕的。」
而身材壯碩的德彬,從小因為體重和體型,遭受的霸凌幾乎像呼吸一樣無時不刻。德彬:「常常把椅子拉開讓我空坐,這是很習以為常的,全班看到也會笑,我就會覺得說,如果能夠讓大家開心,這是我活著的價值,其實那時候價值觀會有點偏差,那次事件比較嚴重是說,他在前一段下課已經拉過一次椅子了,後一段下課他就拿我的圓規插在我的椅子上面,然後在我不注意的時候就坐下去,坐下去整個跳起來,才發現自己屁股被插了圓規,當下我就很憤怒,那次算真的是我從小到大被欺負第一次反擊。」拒絕當沉默者,德彬勇敢站出來,嚴正告戒對方,殘酷的青春 也終於慢慢走回正軌。
2012年教育部制定「校園霸凌防制準則」,明訂導師、任課教師或學校其他人員,發現疑似校園霸凌事件時,應立即通報校長或學務單位,學校應就事件進行初步調查,並於三日內,召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展開處理程序。
根據教育部統計,近四年來全台灣的校園霸凌通報數,大約600件上下,以2018年來說通報數561件,但真正確定霸凌的僅有162件,全台灣的學生有440萬人,每年成立的霸凌件數僅有百件,不及學生總人口數的萬分之一,兒福聯盟質疑,未通報的黑數,恐怕難以估計。
校園霸凌,除了最常見的肢體霸凌和言語霸凌,還有遭到同儕排擠的關係霸凌、從被霸凌者轉為霸凌者的反擊霸凌,與越來越常見的網路霸凌,而校方的態度,往往是處理霸凌事件的關鍵。
其實,校園霸凌事件,最可悲的不是霸凌本身,也不是當事人的無力,而是整個社會的冷漠態度和不作為,這比「惡」還要可怕。抵制霸凌,除了教孩子學會尊重個別差異,營造友善環境,孩子也該學習,遇到不公平的對待,如何為自己和為他人發聲,畢竟,只要有「一個人」願意站出來,不論是陪伴他、幫他說一句話、還是站在他那邊,就有機會逆轉悲劇、創造不一樣的結局。
新聞來源:華視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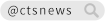


讀者迴響